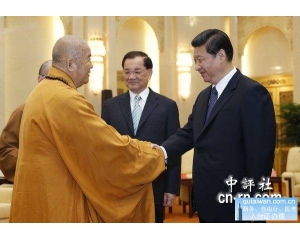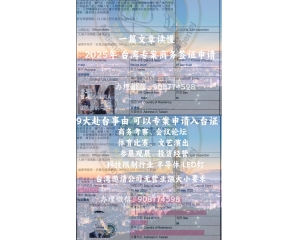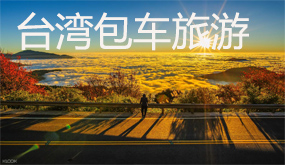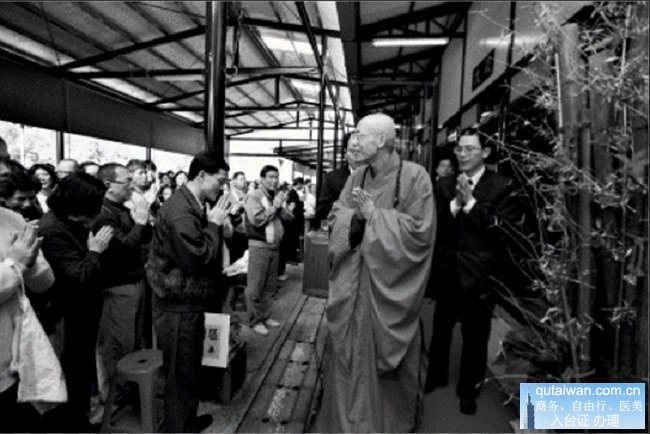
一、鄭氏時代
佛教之傳入臺灣,吾人推測很可能是始自唐代。然有信史可征,則為鄭成功率軍渡臺之后。永歷十五年(即一六六一)延平郡王鄭進軍臺灣,改臺灣為東都,改赤嵌城為承天府,置天興及萬年二府,建兵農合一之屯田制。鄭氏三代經營臺灣共二十二年,其間與佛教有關者,據連雅堂通史記載云:東寧初建,制度漸完。延平郡王經,以承天府之內,尚無叢林,建彌陀寺于東安坊,延僧主之。由此可知彌陀寺即為臺灣最早之佛寺。又據高雄縣左營興隆寺碑記載:大清康熙乙巳年(即四年,公元一六六五),臨濟正宗僧勝芝和尚及其徒茂義、茂伽三人來臺灣。見龜山(即現舊城之龜山)之秀麗,形景而有奇,就處塔蓋草亭。登山伐木,烹茗濟渴行人,嗣募建寺宮。連氏通史宗教志又載謂:嘉義火山碧云寺,為康熙十四年來自福建之僧參微,往錫龍湖巖。一日偶至此地,以其山林之佳,遂辟茅結廬,奉龍湖巖之佛祀之。朝夕誦經,持戒甚固,這就是鄭氏時代,臺灣最初之寺院,以及由內地來臺的幾位僧伽之情形。
至于鄭氏時代所建之寺廟,可以認為佛教寺院者,根據清代之各府縣志記載如下:在寧南坊有觀音堂、準提堂,在鎮北坊有觀音亭、萬福庵、赤山堡,六甲之龍湖巖等六處。
當時佛教之活動情況,惜無正史可稽,即有亦是稗言野史,不足憑信。而在家居士對于佛教有修養者,卻大有人在,多為明末遺臣,痛心亡國,不愿再仕,乃變服為僧,或終身持齋,或終日誦佛經自娛,如沉光文字文開,少以明經貢太學,福王元年授太常博士,聞桂王立粵中,走肇慶,累遷太仆少卿,永歷三年來臺,其后為人進讒,幾遭不測,故變服為僧。李茂春字正青,隆武二年舉孝廉,善屬文,永歷十八年來臺,卜居永康里,日誦佛以自娛。林英字云義,崇禎中,次歲貢知昆明縣事,后祝發為僧,間道至廈門,入臺灣。張士,崇禎六年副榜,明亡入山,耿精忠之亂后入臺,居東安坊,持齋念佛,倏然塵外。另有明魯王女,聰慧知書,工刺繡,適南安儒士鄭哲飛,生一男三女,夫歿來臺依寧靜王以居,晚年持齋獨處,邑人欽之,以為女師。前述六人,實開臺島在家學佛之先河,且為臺灣早期佛教史之珍貴一頁。

二、清代時期
康熙二十二年八月,鄭克塽降清,于是臺灣成為清朝版圖,海禁開后,佛教隨之而流入。靖海將軍施瑯就寧靖王府邸改建天后宮。鄭氏部將,義不帝胡,并借佛教之名,潛身為僧者甚眾,并在暗中窺復明室,加以清室攻臺之敗將,亦多薙發為僧。真正宣揚佛教之教理者,當亦不乏其人,惜臺灣變亂迭起,文獻幾乎湮沒,今由臺府縣志及寺廟現存之金石稽查,仍能略見當時二三有名之高僧,如海會寺(即今臺臺開元寺)之住持釋澄聲,別號石峰,戒行素者,并擅書畫詠吟。其二為釋照明,住錫彌陀寺,日夜誦經不輟,工寫蘭菊,飃逸群倫。其三釋志愿,別號逢春,銳志苦修,居竹溪寺(臺南市南側),暮鼓晨鐘,諷誦自警,雖大風疾雨不廢,數十年如一日。其四如蓮芳,號藕船,住持三官堂,好吟詩,究醫術,著有浣花吟詩。海會寺原為北園別館,為鄭經之母董氏養老之所,康熙二十九年改筑為寺,翌年四月改稱海會寺,開山僧為志中禪師,前述之釋澄聲是該寺第四代祖師。至于釋照明住錫之彌陀寺,是鄭經時代所建。康熙五十八年,武夷僧一峰,募建西堂及僧房,始成寺院。釋志愿所住之竹溪寺,乃康熙四十八年僧慧珍添建落成。
清代在臺最初建設之佛寺,為臺南法華寺,其次是臺南黃檗寺。康熙以后,乾隆年間,寺院之建設,有高雄鼓山之元興寺,同時桃園龜侖嶺,高雄岡山亦有佛寺之添建事實。嘉慶以后則神廟增加,而佛寺反少矣!
臺灣之白衣佛教,又稱齋教,此種團體分三派:是龍華派、金幢派、先天派,都由大陸傳入
臺南龍華派之齋堂是臺灣最初之齋堂,系由福建傳入,此中又可分為四派:福州城內傳來者為復信堂派、福清縣觀莊善福里一是堂派、興化府仙游縣白角嶺漢陽堂派、第二十三祖林普定所創立之中和派等。此四派在臺灣之分布:一般認為臺南是復信堂派,臺中是一是堂派,臺北、新竹是中和堂派,宜蘭是漢陽堂派,大抵是清朝嘉慶以后傳來的。金幢派之開祖王太虛,是龍華派開祖羅因長女之徒,生于北京附近,為公元十六至十七世紀活躍的人物。著有四十二部經,三祖以后,傳入臺灣。
先天派開祖,亦傳為達磨,事實上可能是黃德輝。咸豐十一年(公元一八六一),黃昌成建設臺南報恩堂,李昌晉到臺中,宣教于北部,光緒年間澎湖地方亦奉之。
三、日據時代
光緒二十一年,中日甲午戰爭,清廷敗績,割讓臺灣,由于日本佛教之曹洞宗、真宗等宗務院早已派員隨軍布教,加以當時臺灣之僧伽與教友亦以加入日本佛教為榮,前者則參加釋宗之曹洞宗和臨濟宗妙心寺派,居士或則加入禪宗、真宗東西本愿寺、凈土宗不等。
日據時代,對于齋教贊揚極力,謂其不剃發染衣,在塵不染塵,是真正佛法。然白衣教徒各有職業,無暇顧及佛教教理,所以有礙佛教之發展。他方面傳授臨濟宗之出家佛教,又與大陸隔離,因此成為孤立狀態。即或是初來臺灣,尚為可觀,但無大叢林之道場,乃至傳戒修鏈等法會,自然一代比一代衰落,且因內地僧伽亦少渡臺,所以內臺佛教之交流杜絕。
日本佛教各宗相繼來臺者,以臨齋宗、曹洞宗、天臺宗、凈土宗、真宗本愿寺派、真宗大谷派最有勢力。此種帶有強制壓迫之佛教,造成一種奴化的佛教,致使臺省僧眾無自立發揮之可能。僧尼要受教育,只有去到日本接受佛教式教育,所以他們對于佛法雖有了認識,但他們對于出家的生活卻不習慣,因此臺灣的比丘完全是日本化─娶妻吃葷,也是比丘漸少,比丘尼日漸增多的原因。
自臺灣時間初年,西來庵事件發生以后,白衣齋教牽累甚多,因此齋教三派不得不出以自衛,組織齋教聯合會,計參加此會的齋堂有七:
1.金堂(幢)派:西華堂、慎德堂。
2.先天派:報恩堂、崇德堂。
3.龍華派:德化堂、化善堂、德善堂。
臺灣時間元年,齋門三派之聯合共名曰齋心社,合計七堂,每堂每年辦公二次。其公供之期,各堂人眾齊集演說經教。其后臺灣時間四、五年,臺北先天派領袖黃玉階先生,意圖組織臺灣中之宗教,除齋教三派外,聯合佛門僧伽,甚至道士都想羅織在內,因為范圍過大,未獲成功。
臺灣時間十年日本駐臺當局,邀請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住持善慧和尚、觀音山凌云禪寺住持本愿和尚,于艋舺龍山寺召開籌備委員會,以組織全臺佛教徒,齋教各派俱出席。翌年四月四日成立南瀛佛教會,并發行南瀛佛教月刊。以后每年都辦理短期佛教講習會兩次,維持至臺灣光復。
在日據時代,佛教中最活動人物為善慧,臺灣時間五年善慧得曹洞宗本山之援助,建設臺灣佛教中學于臺北市東門町(即今上海路)。代表臨濟宗妙心寺派的本圓,設鎮南學林于圓山臨濟寺內,因經濟無著,僅辦一、二期遂閉校,將學生合并于中學林。
此外有泉州鼓山涌山寺監院覺力,來臺后,于臺灣時間元年建法云寺于苗栗大湖。由于覺力學德兼備,其渡眾之多,可與善慧比肩,其末派寺院多達二、三十軒,稱為法云寺派。靈泉寺派有三、四十所。而觀音山凌云寺派,實與臺南開元寺、高雄超峰寺等同一派,末派寺廟也不在少數。
前述三位高僧,覺力于臺灣時間二十二年入滅。善慧則于臺灣光復之年入滅,本圓并曾做過光復第一任臺灣佛教會理事長,于卅六年圓寂。
四、光復以后
臺灣時間三十四年十月,臺灣光復,本省大德善慧,鑒于正可弘揚正法,乃組織臺灣佛教會,是年底在臺北龍山寺召開成立大會,本圓和尚當選為第一屆理事長。其后,第二屆理事長沈德融,三、四屆理事長宋修振對會務之發展,均能竭盡其力。
三十七年冬,中壢圓光寺妙果和尚,首先聘慈航法師來臺,創辦臺灣佛學院,招收男女學僧有六、七十名,是為臺灣佛教教育的開始。三十八年春,又于基隆靈泉寺開辦佛學院,自后即掀起了佛教青年僧尼,或在家信眾普遍探究佛法的熱潮。
同年,臺灣佛教會,深悉中國佛教總會組織法,乃依照規定改稱為中國佛教會臺灣省分會,繼之各縣市支會成立,分別展開宣教弘法,施診育兒工作。(省分會理事長林錦東每年又舉辦布教師短期講習班一次,組織環島弘法講演,并聘請旅美學人─紐約大學佛學教授張澄基博士返臺講演佛學,收效甚宏。)
三十九年二月,中佛會遷臺正式恢復辦公,臺灣省分會及各縣市支會在中佛會直接督導下,護教衛國的工作,又向前推進了一步,現在,已登記的團體會員有三百六十二個單位,個人會員二萬四千三百五十人。但實際上本省教胞,約有二百五十萬,寺廟三千七百余所。
四十年夏季,大醒法師繼慈老之后,在新竹青草湖靈隱寺創辦佛學講習會,汐止靜修院也接著辦過一年的佛學講習班,印順法師在新竹青草湖福嚴精舍也辦有佛學院,乃后臺灣之佛學苑、佛學專修班、佛學講座、講習會??相繼在全省各地設立,蔚然成風。
文化宣傳方面,最初,僅有臺灣佛教一種定期刊物,然大醒法師遷來佛刊老牌的海潮音,繼之,人生、中國佛教、覺生、佛教青年、今日佛教、菩提樹、大乘、法音等雜志,相續出版,復又有覺世旬刊,四開報紙有波羅蜜問世。此外如修建寺院,翻印經典和佛學名著,也很風行。最彌足珍貴的就是影印大藏經,已于本年初完成,續藏亦在籌印,同時,四十五年十一月在臺北,成立了修訂大藏經委員會,另如,周子慎發起由全省各民營電臺,每日廣播佛法三十分鐘,使之適合現代需求,其他,如佛教歌詠隊、圣樂團的組織,且有自編的歌詞曲譜,代替古式的香贊,更加強了弘法的成效。
四十四年十一月,迎奉玄奘大師靈骨返臺,臺北機場冠蓋云集,極盡一時之盛,為近年來臺灣佛教之罕見。他如印順法師兩度赴菲和演培法師應聘往泰講學,對促進國際文化與友誼,均有貢獻。
前述事宜,都是令人欣喜的現象,如四眾人等,齊能確實以弘法利生為宗旨。在具有許多優越條件下的臺灣佛教,未來的歷史應該是光輝的、燦爛的。